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
 huarenshengsixue@126.com
huarenshengsixue@126.com
-
传真 :
忆胡军师
文/胡星铭
第一次听说胡军师,是2004年前后在书店里看到他写的《哲学是什么》。只是翻了翻,并没有买,因为看到“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那一行字,觉得很民哲。当时我念本科三年级,读了Stumpf的Socrates to Sartre: A History of Philosophy(单斌老师赠送的英文复印本)和罗素的Problems of Philosophy,对西方哲学有一点感觉,但还是决定考个中国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心里想着先打一点国学基础,等英文更好一点,再深入学习西方哲学。在图书馆准备考研时,累了就去看看书架上新到的书,再次碰到胡军师的《哲学是什么》,就又翻了翻。看了十几页后(印象中是关于怀疑论的),觉得写得很好,于是当晚就去书店买下这本书,尽管仍觉得“哲学是美好生活的向导”这一说法不靠谱(多年后,我才了解到当代分析哲学对well-being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同时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与meaning in life也成了主流分析哲学研究的对象)。

第一次见到胡军师,是在硕士入学面试时。面试很紧张,我把平常背诵的东西都忘了,连孟子的“四心”都忘了,只答上来“三心”,最后“一心”——“ 是非之心”——是胡军师为我补充的。后来我了解他的学术取向后,对于他能记得孟子 “四心” 的内容,还是蛮惊讶的。学者可以粗分为两种,一种是爱迪生式的,注重记住知识点;一种是爱因斯坦式的,注重独立思考能力。爱迪生招助手,要考“声速是多少?”之类的知识点。记者拿着爱迪生的试卷去让爱因斯坦做。爱因斯坦说:“能在《百科全书》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下。”哲学系有爱迪生式的学者,以能背诵大量古文为荣,也有爱因斯坦式的学者,不去刻意背诵任何东西。印象中的胡军师,应该是后者。
再后来见到胡军师,是新生开学典礼。他在陈来老师后面做了一个发言,具体讲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说搞哲学要注重方法,并讲了梁启超的一个典故。罗素来中国讲学,梁启超致欢迎辞,讲了一个笑话:“吕纯阳有次遇着一个人,拿手指点一块小石头,就成了一块金子给那个人,那个人不要。再点一块大的给他,他又不要。再点几块更大的给他,他还是不要。吕纯阳很欢喜,以为这个人真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就问他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答道:‘还要把指头给我们。’什么是罗素先生的指头呢?先生把他自己研究学问的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用先生的方法研究下去,自然可以做到先生一样的学问。这不是我们变了第二个吕纯阳,也能点石成金吗?”
胡军师讲梁启超的典故,是否暗示我们应该学习罗素的方法,我不得而知。但我读的国学经典越多,就越喜欢分析哲学,也逐渐能理解为什么严复和王国维要翻译英国学者的逻辑学著作,为什么梁启超注重对墨子逻辑学的研究,为什么胡适的博士论文要研究先秦逻辑方法的发展史,为什么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一再强调“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为什么张岱年最重视的西方哲学家是罗素。到了研二选导师的时候,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分析哲学兼有研究的胡军师便自然成了我的第一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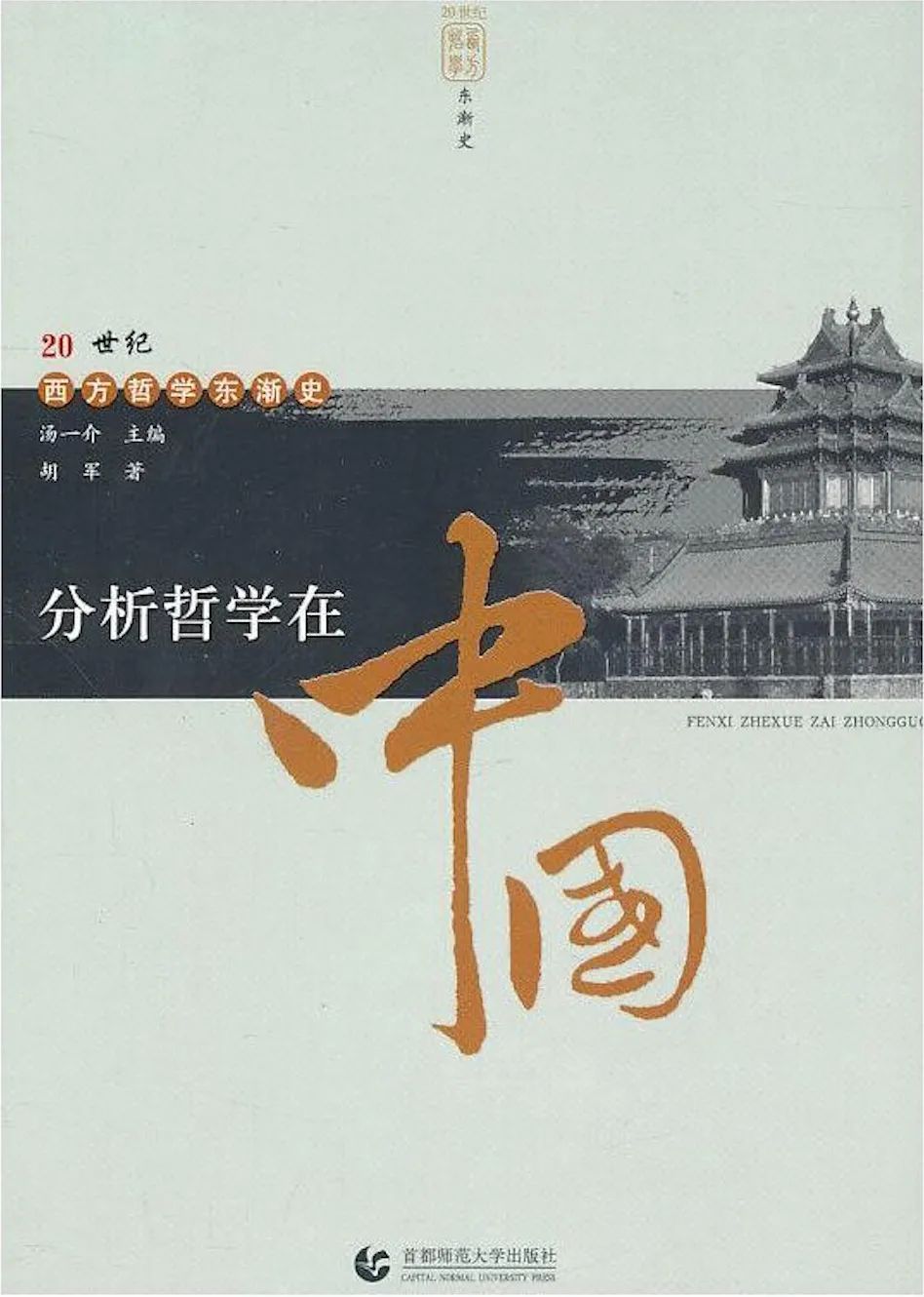
胡军师指导学生,跟系里很多老师一样,是放养式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他的言传身教依旧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讲学逻辑对学哲学非常重要,讲自己年轻时如何自学逻辑,不但激励着我也自学起逻辑,甚至导致我后来去选修了一门非常难的数理逻辑课(邢滔滔老师开设)。他上“中国现代哲学”这门课,主要讲知识论,我的学术兴趣也由此向知识论慢慢偏移。我从他推荐的书目中顺藤摸瓜读了许多当代知识论的论文,坚定了博士阶段研究知识论的决心。他讲自己刚入北大教书时如何小心谨慎、勤奋刻苦,多年后我入南大教书,常常想起他的话,不敢稍有懈怠。
硕士毕业后,我升学不顺利,导致一年的gap。胡军师有点惋惜,跟我说:如果当初选择继续跟他读博士,把硕士期间研究的项目深入下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那时对分析哲学的热情很高,对于自己的现状很不满,实在想换个环境脱胎换骨一次。后来我去美国读博,胡军师很开心,跟我说:“之前中哲专业的学生出国,一般都是去东亚系或宗教系,你去哲学系学很好,可以系统地学习分析哲学”。我说,我其实是想打一点坚实的西方哲学基础,将来像胡适和冯友兰一样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他听了有点失望,因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常常是神谕或领导讲话式的,天苍苍野茫茫,缺乏系统明确的论证,不需要再“认真学习,深入领会”,而“急需现代化”。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途径——问题与方法》一文中,他写道:
中国传统思想往往以意味隽永的格言、成语来阐发的。《论语》采取的就是这样的问答体。一问即有一答。没有讨论或论证的过程。学生也很少质疑孔子所提供的答案。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来实践或持守孔子所提供的答案。而且由于过度注重表达的形式,而不注重对所表达的内容的论证,于是也就根本谈不上系统明确的论证所需要的方法论。尽管有对话,但是由于对话仅仅表现为问答的形式,即由学生问,师长答。师生之间没有讨论,更没有论证。其结果就是,对话之间不需要相关的思辨规则的逻辑技巧及学理性的东西以为支撑,而完全诉诸于提供答案的人的权威或圣人的人格或地位。此种情况一致延续至今,几千年之后的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思想,不会做思想的论证。一旦有了自己的意见,反而会为自己的思想或意见的对错而惶恐不安,急需要依靠圣人或权威或领导来确认或指定。这种思想传统为思辩理性的进步与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我们没有衍生出高度精密的思维科学及其方法论就是明显的一例。同时,这样的思想传统内也不可能出现对自然现象、社会结构及人文做分科治学的研究,因此也就历史地妨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学术的繁荣。近百年来,西方的学术一旦进来后,我们就突然发现自己处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之下,失去了自我,丢掉了文化的主体性。其结果也就是丢掉了自己的话语权。目前不少学者在急切地呼吁,要有制度自信,要有理论自信,要抢回话语权。但他们根本就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所谓的话语权不是能够随便说抢就能够抢回来的。因为科学、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军事等领域内的话语权的真正基础就是得到了系统论证过的知识理论体系。而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这一段话有“五四”那一辈学者的遗风。我特别赞同胡军师“中国哲学需要注重明确的论证”这个观点。但我认为早期中国哲学并非不注重明确的论证。《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许多中国哲学经典,在明确的论证方面,并不输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只是这个传统后来因为一连串的伟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易白沙语),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虽然并没有中断)。同样,质疑老师的观点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传统。禅宗有一个著名故事:云崖法师死后,他的弟子洞山和尚设斋祭奠。别人问洞山:“尔肯先师也无?”洞山答:“半肯半不肯。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说“半不肯”才算对得起先师,跟西方哲学家说的“用批评表示敬意”,是一个意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注重明确的论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质疑权威的观点。
在正式确立师生关系之前,胡军师请我在学校留学生中心的勺园宾馆吃饭。他点了一份牛肉,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年轻人要多吃一点牛肉”。后来有一次跟他喝酒,他劝我多喝一点,我说:“我不行了”。他一本正经地说:“男人不要说自己不行”。我大笑,那一次喝了很多。胡军师也跟我讲了学术界的很多掌故,以及他对许多著名学者的评论。工作后,我曾打算找个时间跟他合作做一本对话体回忆录,把他知道的各种有趣的事以及他对这些事的看法都记录下来,在他百年之后出版。但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糟心事也多,一直拖着。现在来不及了。
2022年8月19日初稿,8月23日改定

 最新发表
最新发表